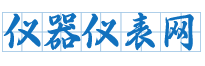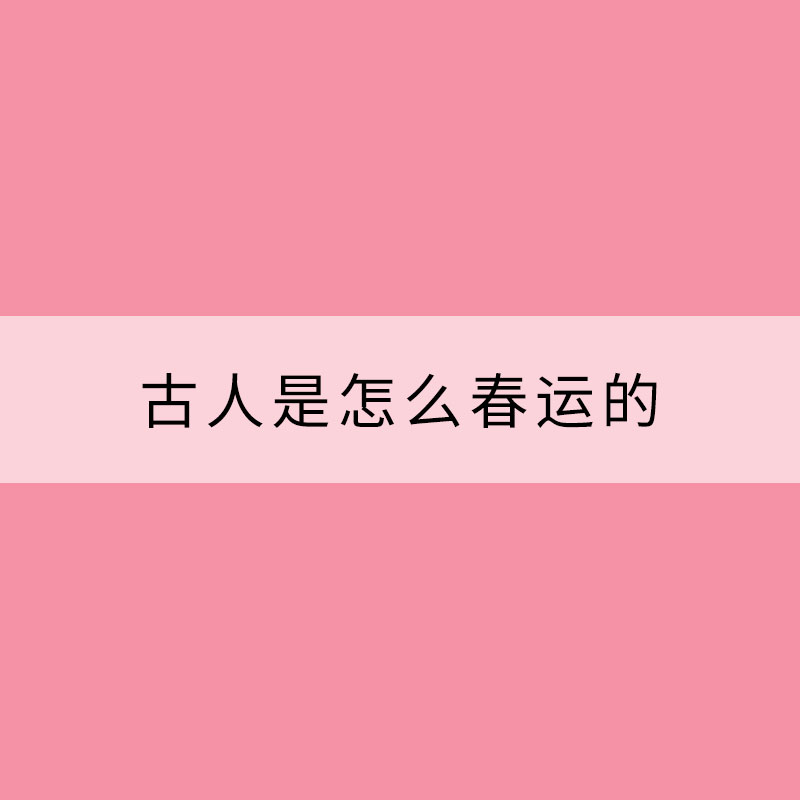
其實(shí),自從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文化中有了春節(jié)回家團(tuán)聚的習(xí)俗,就有了春運(yùn)。古人們雖然因條件所限,不像現(xiàn)代人一樣大規(guī)模在外工作打工,但是古代官員、在外經(jīng)商的商人、在外游歷的文人、外出謀生的人,也會(huì)爭(zhēng)取趕在春節(jié)前回家。
在古代,春節(jié)也是放假的,比如宋朝。據(jù)宋史筆記《文昌雜錄》記載,元日(春節(jié))、寒食、冬至各放假七日;天慶節(jié)(正月初三)、上元節(jié)、天圣節(jié)(皇帝母親生日那天)等也都放假,這么前后連起來(lái),差不多這一個(gè)月都在放假。唐朝雖然沒(méi)有宋朝這么多假日,但也出臺(tái)了不少人性化的政策,比如:父母住在三千里外,每隔三年有30天的定省假(不含旅程);父母在五百里外,每隔五年有15天的定省假。清朝中期,春節(jié)和寒假的假期均延長(zhǎng)至一個(gè)月。
即便有這些在我們現(xiàn)代人眼里看上去很寬松的假期,但是因?yàn)楣糯煌ú话l(fā)達(dá),路況又差,道路崎嶇不平,碰上下雪天,更是泥濘難行,古人們千里迢迢回一次家,動(dòng)輒耗費(fèi)數(shù)月,實(shí)屬不易。
南朝時(shí)的江淹,其《別賦》中有一句“舟凝滯于水濱,車(chē)逶遲于山側(cè)。棹容與而詎前,馬寒鳴而不息。”里面有舟、車(chē)、馬這三種中國(guó)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。而到了北宋,在《清明上河圖》里,交通工具更是五花八門(mén),比如人力車(chē)、轎子、騾車(chē)、驢車(chē)、馬車(chē)、獨(dú)輪車(chē)、牛車(chē)、架子車(chē)、船等。
在陸路上,古人們主要使用的是牲畜和畜力車(chē)。但是騎馬和馬車(chē)在古代是一種身份象征,通常只有官員才有這個(gè)特權(quán)。一般的平民百姓只能騎驢,直至近代,驢和驢車(chē)都還是民間重要的交通工具,以至于摩托車(chē)大范圍使用后,人們戲稱之為“電驢”。而更窮的人們,就只能“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”了。所以古時(shí)候,考生們進(jìn)京趕考,往往要提前半年多就從家鄉(xiāng)出發(fā),如果有云南的考生要去京師,那一路上說(shuō)起來(lái)都是淚啊。
水路方面,長(zhǎng)江、黃河和京杭大運(yùn)河是那時(shí)候的主要大動(dòng)脈。李白乘船沿長(zhǎng)江而下,寫(xiě)下“朝辭白帝彩云間,千里江陵一日還”,這絕對(duì)是夸張筆法。曾有較真的技術(shù)宅根據(jù)酈道元《水經(jīng)注》中對(duì)白帝城和江陵之間的距離描述,計(jì)算帆船的大致時(shí)速,得出結(jié)論:就算日夜兼程,一路上不投宿不下船吃飯,也至少得三天。
京杭大運(yùn)河自元朝全線貫通后,是咱江南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。杭州歷史學(xué)會(huì)的丁云川說(shuō),明清時(shí)候,坐著小船從北京到杭州,一路上大概要一個(gè)月左右時(shí)間。這在慈禧傳記中也有體現(xiàn),據(jù)說(shuō)慈禧小時(shí)候在徽州生活,后來(lái)父死返鄉(xiāng)(北京),從徽州沿新安江順流而下,坐船直走京杭大運(yùn)河,整整一個(gè)月。
由于回一趟老家是如此的不易,因此古人們很多都趕不上除夕那天回到家,或者干脆就不回家了,只能用飽含鄉(xiāng)愁的詩(shī)歌,傾訴思念親人的愁悶。
比如唐代詩(shī)人戴叔倫寫(xiě)過(guò)《除夜宿石頭驛》,“一年將盡夜,萬(wàn)里未歸人。”除夜就是除夕,戴叔倫是江蘇人,晚年任撫州(今屬江西)刺史。寫(xiě)該詩(shī)時(shí)他正寄寓石頭驛(今屬江西),可能要取道長(zhǎng)江回故鄉(xiāng)金壇。
晚唐詩(shī)人崔涂是杭州富春江一帶的人,曾長(zhǎng)期旅居四川和陜西一帶。他在《除夜有懷》中說(shuō),“亂山殘雪夜,孤?tīng)T異鄉(xiāng)人。漸與骨肉遠(yuǎn),轉(zhuǎn)於僮仆親。”遠(yuǎn)離親人在外久了,連僮仆也感到親切,更表達(dá)出了思鄉(xiāng)之切。
蘇軾也遇到過(guò)春節(jié)不能回家的情況,他的《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》作于宋神宗熙寧六年(1073),蘇軾奉命前往常州等地賑濟(jì)災(zāi)荒途中。可見(jiàn)古時(shí)的官員,如果身有要?jiǎng)?wù),即使春節(jié)也得加班加點(diǎn)。
這么一對(duì)比,如今的我們真是幸福得冒泡。高鐵、飛機(jī)已經(jīng)讓“天涯若比鄰”成了現(xiàn)實(shí),網(wǎng)絡(luò)通訊業(yè)的發(fā)展讓我們可以跟親人朋友“隨時(shí)隨地通信息”。不過(guò),那份詩(shī)意的鄉(xiāng)愁和對(duì)親人的牽掛,卻是永恒不變的。